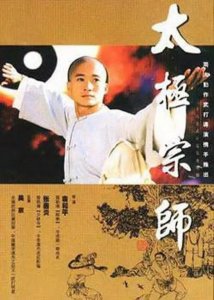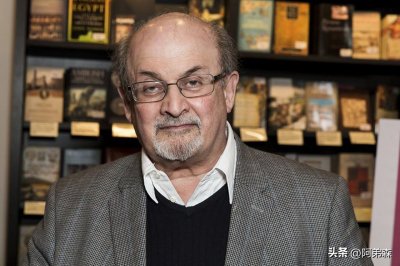《掠妻》作者:白鹭下时
《掠妻》
作者:白鹭下时

简介:
京城陈留侯府二子原是双生。
哥哥风姿卓越,文武兼备,如圭如璋。
弟弟鲜衣怒马,卫国戍边,亦是万里挑一的好儿郎。
识茵嫁的是弟弟,谢家二郎谢云谏。
他与她在灯会上相识,遂三书六礼聘她过门。是夜花影满地,凤烛光明。识茵羞怯抬眸,柔声唤身前皎若芝兰的新婿:“郎君。”
明眸翦水,正似秋水落芙蕖。
四目相对,烛影深深。她看见新郎深邃目光蓦地一沉。
他冷淡应了一声:“嗯。”
婚后,婆母说郎君性子冷淡,要她多主动些,识茵也照做了,日夜痴缠着他。夫婿虽不过分热情,却也没拒绝她的主动,夫妻生活尚算融洽。
直至某日,真正的谢家二郎回京省亲,将要看望新婚的妻子——
新妇所居的园舍突遭大火,赤红色火焰一望无尽。
所有人都当新妇已死,唯识茵知晓,她被锁在一间密室内,做下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她那个夜夜同榻而眠的好“夫君”——谢家大郎谢明庭。
——当日,误以为夫婿战死,婆母为沿继香火,遂命夫兄兼祧两门,与她成婚。
她曾以为的夫妻恩爱琴瑟静好,只不过是一场骗局……
他的手如刀锋抚过她脸颊。
耳后响起的声音隐忍喑哑:
“茵茵……先与你遇见的是我,与你成婚的人也是我,凭什么,你要选他?”
娇柔心机小美人 vs 斯文败类·伪高岭之花哥哥&活泼漂亮爱黏人小狗弟弟,男主是哥哥,双c
精彩节选:
永贞三年,秋。
七月流火,洛阳城总算减了几分暑气。正平坊顾氏家宅内,晴空轻烟袅袅,堂下杨柳依依,一排排檐灯穗子在金风中悠悠摇荡,一切都是美好的初秋图景。
檐灯之下,顾识茵姿态娴静,倚在美人靠上刺绣。
飞针走线间,一只栩栩如生的麒麟于青灰色的丝帕上渐渐显现。
她衣饰简朴,不施脂粉,亦无钗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只在斜挽的乌云上簪了几朵玉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一张清婉的美人面,映着悄悄探入檐下来的白玉山茶,花面交映,光耀玉润,叫人几乎睁不开眼。
对面,一个小丫鬟捧着篾箩,仰着头巴巴地看了她半天。
女郎生得可真好。
小丫鬟在心间暗叹。
怪不得呢,即使生在顾家这样的小门小户,父母双亡,寄人篱下,也能被陈留侯府的二公子一眼相中,自灯会上惊鸿一面后,巴巴地求了母亲武威郡主上门提亲。
她至今都记得,侯府来府中下聘的那天府中是何等高兴,郎主女君惊讶得不能置信,阖府上下喜出望外,连那一向与小娘子有隙的四娘子都转了性,“阿姐”、“阿姐”叫得亲热。
是啊,谁能不高兴呢,那可是陈留侯府。京中谁不知道陈留侯府三百年清贵望族,既是外戚又有军功,一对双生子皆是人中龙凤。
她们那位准姑爷,更是十七岁时就点了鹰扬将军,十九岁升任正三品的龙骧将军,跟随凉州公出战沙场,战功赫赫,京中想嫁他的贵女可以从城东一直排到城西。
反观家中,郎主生前只是个太学的六品小官,夫人也是画工之女,与“清贵”二字毫不沾边。
小娘子失恃又失怙,长在伯父家。但即使是郎主,也仅仅只是个从五品的主事。
这门亲事,真真切切是她们顾家高攀了。
但郡主却说是老爷生前和已去世的陈留侯定的,并非高攀,下定时又送了许多的彩礼,里里外外给足小娘子面子,洛阳城中无不艳羡……
忆起下聘那日侯府丰厚的赏钱,小丫鬟对这桩婚事的祝福都真心起来:“女郎绣得可真好,活灵活现的,就跟真的一样。历来麒麟最是难绣,您又绣了这么久,丝丝线线都是相思,咱们姑爷一定会喜欢的!”
“又贫嘴。”识茵无奈地收起花绷,轻在她头上敲了一下,“还没成婚呢,乱叫什么。”
“反正是姑爷嘛,早晚也得叫啊。”小丫鬟道。
又满脸堆笑地祝福:“女郎对姑爷那样好,姑爷一定会喜欢您的。你们一定能长长久久,百年好合!”
她本是说的吉利话,自己脸色却一变,忍不住朝女郎看去。
识茵面无异色,正摊开花绷看着那未绣完的麒麟,横波双目中透出一丝浅笑:“若真能如此,也就好了。”
主仆二人又说着话,讨论起该用何种丝线绣作配的祥云,堂下忽传来一道声音:“哟,阿姐在忙呢。”
识茵回眸,一个身着淡粉衫子、石榴红裙的少女眉目倨傲地走进院子,身后还跟着数个抬着箱笼的侍女。是她的堂妹,顾四娘。
“阿姐可真有闲心。”她笑盈盈地走进来,“马上就要出嫁了,你不做正事,倒有闲心在这里绣帕子。”
“是给姐夫绣的么。”
顾识茵将帕子往篾箩里一收,并不起身。她淡淡问道:“四妹妹怎么来了。”
“妹妹来给三姐姐添妆啊。”顾四娘道,“听闻三日后陈留侯府就要迎娶三姐姐过门,姐姐大婚在即,妹妹真是好生羡慕。”
虽是恭贺的话,她眉梢眼角实藏挑衅。识茵道:“是吗?婚期已经定了吗?”
“是啊。”顾四娘笑吟吟道,“昨天就派了人来,说婚礼一切照旧,只是姐夫不良于行,恐怕不能来迎亲。到时候他们派人来接,姐姐自己过去就行了。想来阿父阿母很快就会告诉姐姐这件事。”
“三姐姐,你这一嫁可就成了将军夫人了,将来富贵,可不要忘了姊妹们。”
女孩子的笑意里有种残忍的天真,更多的却是幸灾乐祸。识茵淡淡莞尔:“那么,四妹妹打算给我添些什么呢?”
顾四娘唇角抿过一丝讥讽,指示侍女将那口抬起来的红木箱子打开:“安平居的鞍鞯,汨罗堂的弓,还有西市的蹴鞠,听闻姐夫征战沙场弓马娴熟,于蹴鞠一道也是国手,姐姐你也该学一学,省得婚后连个共同爱好也没有。”
“对了,还有这些绸缎。上好的苏锦,妹妹我自己都舍不得穿,拿来送姐姐,是怕这么鲜亮的颜色,阿姐出嫁后就穿不上咯!”
顾四娘笑起来,身后的侍女也跟着笑得前仰后合东倒西歪。识茵身边的小丫鬟气得脸都歪了,这……这哪里是添妆,分明是给女郎添堵!
送马鞍,蹴鞠,是因为这些东西,准姑爷用不上了。
说小娘子日后不能穿鲜亮的颜色,是在恶毒地诅咒她,过门即守寡。
是的,这桩婚事虽好,但小娘子要嫁的那位谢二公子却已很不好了!就在一个月前,他被派往江南查一桩军饷贪墨案,在建康遭遇山匪,身受重伤,经脉尽断。
事发之后,陈留侯府不愿退婚,坚持要娶小娘子过门冲喜。而郎主女君,也因早将聘礼挥霍一空而巴不得将小娘子嫁过去抵债,是而在昨日陈留侯府的人上门商议婚期时,十分痛快地答应了。
眼下,阖府都知道了三日后女郎出阁的事,唯独她自己被瞒在鼓里。
当然,现下她也是知道了。可这样的情况之下,她嫁过去不是守活寡吗,她才十六岁啊,为什么要搭进去一辈子呢?
家中甚至还在传,她们的那位准姑爷,已经活不过今年了。而以那位武威郡主的护子心切,说不定,还会让女郎下去配冥婚……
想到这儿,小丫鬟眼眶一酸,眼中慢慢聚起了热意。当事人识茵自己却只轻飘飘瞥了那些宛如闹剧的礼物一眼:“那我就收下了,多谢四妹妹为我添妆。”
一拳打在了棉花里,顾四娘神情微僵,还想再刺她两句,识茵已然越过她,朝屋中去。
她面上毫无反应,反倒衬得顾四娘一群人像上蹿下跳的小丑。顾四娘心神微凛,又很快调整过情绪来,于心中轻嗤。
都是碧玉年华的少女,有谁会想去伺候一个残废,和他生活一辈子呢?顾识茵,只不过是强撑出的不在意罢了。
她朝前方喊:“姐姐如此淡定,莫非已经想好了退路么?”
“也对,二公子不行,不还有个大公子么?听说他们俩可是双生呢,这做弟弟的不行,洞房花烛夜一样可以让哥哥代劳啊。”
“所以啊,新婚之夜姐姐可得看仔细点,别像你娘一样,又搞出有堕顾家门风的事!”
她话音才落,识茵已停下脚步,回过眸来:“你说够了没有?”
“魏律,诬告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者,加所诬罪二等,何况是从四品的大理寺少卿。妹妹既然对咱们的谢少卿这般感兴趣,不妨亲去向他求证此罪该怎么判。或者,我帮你问?”
她难得地动怒,眼中有锐利的刀锋。顾四娘恨恨噤声。
是了,顾识茵未来的大伯,陈留侯府世子,永贞元年圣上钦点的状元郎,正是从四品的大理寺少卿,任职大理寺。
传闻他性情严厉,不苟言笑,断案亦铁面无私,但凡状子送到他手中,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黎民百姓,都逃脱不了应有的罪罚。这话若真传到他耳中,自己的确讨不到好。
她今日来不过是一逞口舌之快,又没真的蠢到得罪陈留侯府。飞快地朝堂姊福了一福:“妹妹只是担心姐姐而已,既然姐姐心中明白,妹妹就放心了。”
随后,她又指挥丫鬟搬起她送来的那一箱礼物,果断地离开了。
小丫鬟依旧为了方才那通阴阳怪气的话生气,识茵却面无表情,继续往屋中走。
事实上,她一点儿也不在意方才堂妹所说。
没脑子的蠢话罢了,生在她们顾家这样的小门小户,更应懂得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盼着姊妹过得好才是。竟也学起洛阳高门里那些姊妹互相攀比的坏毛病,难得她嫁得不好,就会对顾家、对四娘自己有助益?
至于婚事……
脚下步子微滞,识茵眼前浮现起元宵灯会上少年人清朗俊美、言笑晏晏的一张脸来。
灯火流照,灯明月皎。
他提着一盏梅花宫灯,隔着茫茫人海唤她。
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在下姓谢名云谏,改日必当请母亲来府上提亲。
他说你不许嫁给旁人,你要等着我,我一定会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夜流星如雨、棋逢对手,的确是很美的初见。可实际上当时的她是有些害怕的。因为当晚设那局棋,她的目标其实不是他。毕竟以她的家室,实在不敢攀扯到陈留侯府头上……
她没想到和她下棋的会是他,也没想到他会娶她,之后三书六礼,一切都是正妻的待遇。
后来他们通过信,通过信笺内容也可看出他是个赤诚明朗的青年郎君,他在信里同她约定,大漠孤烟、黄河落日,他们都要一起去看……
所以,她愿意的。
就算他真的伤重,她也愿意陪他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此后,也正可顺理成章地摆脱这个“家”。
而她的那位大伯……
识茵眼中浮现出几分恍惚。
她愿意嫁去谢家,除却对未婚夫的好感与同情,还真是有几分是因为他。
三日后,陈留侯府的迎亲队伍如期上门。
被派来负责迎亲事项的是陈留侯府的陈管事,队伍盛大而喜庆,将顾家所在的正平坊堵得水泄不通。
礼仪即毕,识茵手持障面的团扇,被侍女扶上侯府迎亲的马车。车外鞭炮乍起,鼓乐齐鸣,一片乱糟糟的闹哄之后,张红悬彩的马车开始走动起来,整个队伍有如一条赤龙在沟壑里游动,一眼难望到尽头。
附近百姓争先恐后地跳上坊墙,向队首看去——一应都是迎亲的规制,独独没有本该高头大马走在最前面的新郎。
有不明就里之人,开始议论:“怎么不见新郎。”
“没听说吗?侯府的二公子受了重伤,就剩一口气了,这会儿迎顾家娘子过去,就是为了冲喜呢!”
“都不能迎亲了,难道还能行事?那一辈子也就只能守活寡了,小娘子嫁过去得多委屈呀!”
“对了,那位二公子不是还有个状元郎哥哥吗?听说还是双生子呢,要我说啊,这反正都长得一样,干脆洞房夜就叫兄长代劳得了。反正新妇们也分辨不出来……”
人群中爆发出阵阵哄笑,淹没在近乎喧天的鼓乐声里,悬金饰玉的婚车中,识茵却是听得分明。
双生子……状元郎……
她知道他们说的是谁,是她那位素未谋面的大伯,陈留侯府世子谢明庭。
听闻他与她的夫君虽是双生,气质却迥乎不同,一眼就能分辨出孰兄孰弟。夫君习武,他便习文,夫君性格跳脱开朗,有如雄鹰幼麟,他便沉静深邃,有如溪涧美玉。
然后就是前年的春闱,他连中三元,兼又相貌俊美,风姿卓荦,被女帝亲口夸赞为“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听闻,女帝的正牌丈夫楚国公为此好一顿吃味,遂在京中传为美谈。
此后入职大理寺,位列少卿,也是出了名的行事公允,断案如神。
也是因此,被人这般调笑,她的第一反应不是生气,因为她的确别有所图。
她六岁那年的元日,父亲去世,母亲回了娘家改嫁,此后便离奇地去世了。
是舅家亲来报的死讯,但她却并不相信,因为母亲临走时曾亲口告诉她,会在端阳节接走她,但也是那一天,传来了母亲的死讯……
视线重新聚焦于团扇上以金丝银线勾勒出的鸳鸯戏水,识茵回过神来,放下了举得有些酸软的手臂。
已经十年了,她依然不肯相信母亲已经去世。她那位大伯正掌管刑狱,有这层关系在,入府后,她想要去求他帮自己找找。
只是听闻大伯性情冷淡严厉不好相处,自己身为弟妹,也应避嫌,事情就得徐徐图之了。
她也不打算回顾家了,就必须在陈留侯府站稳脚跟。
铜驼坊,陈留侯府。
与盛大的迎亲队伍不同,因今日新婚的主角新郎官不便,这场大婚并未宴请宾客过府观礼,府中冷冷清清,唯有新郎所居的麒麟院里才能觑见几分喜庆的红色。
良辰将至,婚车已至铜驼坊,眼下,识茵那位尚未谋面的婆母武威郡主叱云玉萼,却还身在正院之中,等着仆妇前来回话。
“鹤奴还是不肯?”
新点华灯照得她脸上的怒气无处遁形,得了仆妇肯定的回答后又大怒:“真是反了他了!连我这个做母亲的话也不听!去,拿这根御赐的九节鞭去,把他给我捆了来!”
她抽出缠在腰间的软鞭,一抬手,却露了层层赤红袍袖下的素袖,是一个母亲在为死去的儿子戴孝。仆妇心头一酸,哽咽着跪下:
“郡主,世子与二公子感情一向深厚,眼下二公子尸骨未寒,您却让他兼祧二公子的新婚妻子,这,他心里能好受吗?”
叱云氏愈发愤怒:“就因为麟儿已经死了,这个婚,他才必须得成!”
“麟儿连个血脉都没能留下,将来孤魂野鬼无人祭祀,他心里就好受了吗?再说了,麟儿的死府外尚且能瞒住,新妇这个枕边人如何能瞒住?现在新妇马上就要过府了,他不兼祧谁能兼祧?”
外人不知的是,谢家二郎并非身受重伤,而是径直死在了建康,连具尸首也未能运回来。
他是为女帝查军饷去的,显是遭到了报复。初得到消息时,叱云氏近乎晕厥。
但她很快冷静下来,儿子才二十二岁,妻与子俱无,到地下后也孤零零的。所以,他喜欢的姑娘她会替他娶回来,他没有的子嗣她会让顾氏生下,将来过继给他,让他这一脉香火不至于断绝。
至于向谁借种呢?自然就是她的大儿子谢明庭了!
他们本是双生子,当初长子只早生了一刻钟的时间,由此被立为世子。在叱云氏眼里,他占了弟弟的嗣子之位,如今让他代替弟弟和新妇生子,也是情理之中。
只是,谢明庭不同意。
自然,这等荒谬又有违人伦的事,换成任何一个三观正常的人皆不会同意。何况兼祧之事本就敏感,谢明庭又是在大理寺为官,若被有心人诬告为与弟妹通|奸,仕途全毁不说,更会遭至流刑。但叱云氏更在意的,却是长子的忤逆。
叱云氏最终亲自走了一趟。
鹿鸣院与麒麟院只朱墙修篁相隔,青松翠柏,古朴森森,偶有几只雀鸟停留在被夕光照得朦胧一片的人面纹瓦当上,落寞又孤寂。
院中仆妇杂役皆已屏退,金乌西坠,花影满窗,妇人激动的争执声自窗中泻出:“……麟儿是你的弟弟,你一定要这般狠心吗?”
“你弟弟不明不白死在江南,朝廷连他的尸首也不还给我们,只叫我们一味遮掩着,做出他还没死的假象。可新妇子毕竟是个外人,还未知品行,这时候你不去代你弟弟拜堂把人笼络着,事情泄露了可怎么办?”
书案前站着个褒衣博带的青年人,姿容俊美,风仪楚楚,神情掩在入窗夕色下,轮廓如冰玉剔透。
叱云氏发作的时候,他沉默得就好似山峦在水面投下的静影。
待她发作完毕,才淡淡道了一句:“圣上只让我们对外隐瞒云谏的死,并未让母亲自作主张为他完婚。”
“母亲究竟是出于何私心要顾氏女过门,母亲自己心里清楚。”
叱云氏心中有鬼,几乎被这一句噎死。面上仍是哀戚悲态:“是,母亲知道,当年母亲送走了你,偏心你弟弟,你心里有怨……”
“可这些与你弟弟又有什么干系呢,决定是我和你父亲做的,后来你父亲不也把你接回来补偿你了吗?你父亲在的时候就偏疼你,我自然就要疼他多些。况且你弟弟也常常劝我,要多关心你,许多事是母亲自己对不起你……一切都是母亲的错,你莫要迁怒到他身上啊……”
叱云氏说着便恸哭起来,从来以刚强面目示人的将门虎女,哭来竟也一样的肝肠寸断、使人动容。
对面的青年郎君却冷冷地侧过眸来,目光森冷,如剑如矢,叱云氏余光瞥见,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他竟还记在心里!
他是她九死一生生下来的,自然什么都该听她的,过去的那些事,难道还抵不过她的生育之恩么?
所幸只是一瞬,他目光轻飘飘地自她身上掠过:“母亲多虑了。”
“阿弟的死,儿也很意外。”
青年郎君长睫微敛,如金石缄默无声,仿佛方才一霎而过的寒芒剑影只是叱云氏的错觉。她微愣了一刻,仍是苦苦哀求:“他是你的手足至亲,你就替他和顾氏拜个堂吧……他长到二十二岁,还是头一回如此喜欢一个女子,巴巴地央我去提亲。”
“鹤奴,就当是母亲求你了不成吗……”
室中清漏沉沉,落针可闻,窗边则隐隐约约传来喜庆的唢呐声,是新娘的婚车近了。
青年依旧无所动容,置若罔闻。正当叱云氏欲以一跪相胁迫时,青年终于淡淡开口:“知道了。”
“母亲请回吧,容儿更衣,再见新妇。”
一直到步出鹿鸣院的时候叱云氏还有些想不明白。这,这怎么又同意了?
这个儿子是寤生,生产的时候叫她吃了好些苦头,加之他幼时曾被道士言两兄弟命理相克,七岁之前不得共存,武威郡主私心里更喜欢小儿子,厌恶寤生的长子,遂将他送去了建康故宅,寄养于族人家中,待被接回后性情冷淡,所以从来就不大喜欢他。但母子间也从未起过大的冲突,他缘何会用那般仇恨的眼神看自己?
叱云氏心思惴惴,不得其解。一旁的心腹秦嬷嬷却于此时插话道:“郡主方才何必把话说得这么直。”
“青年郎君们大多性情高傲,何况是咱们连中三元的世子爷?他对二公子的兄弟情谊是真,可他有自己的自尊也是真,身为男子,又有谁愿意去做旁人的替身呢?您把话迂回着说,世子爷也就不会忤逆您了。”
当局者迷,郡主偏爱二公子,与世子亲缘淡薄,也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子。
但她们这些做下人的可都看在眼里,世子他,从来就不喜欢被当成二公子,否则也不会执意长成与二公子截然相反的样子了。
武威郡主不以为然:“他是我的儿子!自然我叫他做什么都是应该。”
二人的说话声淹没在影影绰绰的喜乐声中。窗边,高大俊美的青年仍负手而立,透过窗前一丛婆娑花影,面无表情地看向西边红绸遮月的麒麟院。
身后的桌案上,静静摆放着一套方才送来的喜服。侍女小心翼翼地提醒道:“世子,时辰快到了。”
“知道了。”他漠然应,“你出去吧。”
事实上,弟弟的死,谢明庭从来就不是很信。
说来或许没人能信,他与弟弟既是双生,便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心之感应,此番弟弟被女帝秘密派往江南,他确有几次察觉到他的紧张,但并非致命的威胁,更不可能令他赴死。
云谏,应是被圣上留在了江南,假托病重回京,在替圣上查些什么。越做出这些遮遮掩掩之事,才越叫圣上想查的人相信云谏的“死”。
母亲将顾氏女迎进门自是为了她的私心,但若云谏假死之事因之泄露,在陛下面前却不能交代。
喜房里,识茵已经等候了多时。
没有宾朋满座,也没有高堂见证,婚车在侯府门前停下后,她被径直送入新郎的这一间麒麟院。
触目皆是红色,门前两个红灯笼映得阶下一片朦朦胧胧的绯色光辉,随秋风轻轻摇漾在夜色里,仿佛天地万物都在这大喜的颜色里沉醉。
新房中唯盛列着合卺、同牢所用的礼器,案前,识茵安静地跽坐着,因新郎未至暂时放下了掩面的团扇。
新郎久不至,房中近乎窒息的安静,一旁服侍的侯府侍女低声安抚她:“少夫人且耐心等一等,二公子很快就到了。”
她微微笑着颔首,红烛如水,映照得少女一双春澜秋水的眼潋滟生辉,惹得侍女们尽皆看呆了眼。
这位新妇子生得可真美丽啊!可惜二公子英年早逝,竟连见新妇一面也没见上。
再一想到郡主的打算,房中几名知情的侍女皆不由朝她投去同情的目光,□□之事何其荒唐,也不知这位小门户出身的少夫人能不能接受。
不知过了多久,房门外终于传来一阵脚步,尔后是门外侍女恭敬小声的行礼声:“二公子。”
识茵拿起障扇,横在了脸前。
贴着囍字的门扉在寒夜微风中轻微吱呀,一道松竹般俊挺的身影被门外檐灯照进,投射在红烛潋滟的地板上。
侍女们福身行礼,团扇之后,识茵心神微凛。
郎君,他怎么是走着过来的?
她不明就里,只攥着那柄金丝团扇掩去神情。对面,新郎已经掠过了门边摆放的多宝架,立在了桌案那头。
他身着原为弟弟准备的喜服,倒也算合身。暗金麒麟兽纹玄衣裁剪得体,赤色织金带扣出精瘦纤窄的腰身,身姿颀长,宽肩细腰,在被烛光晕出的一方光明里,身如玉山华岳。
房中服侍的尽是叱云氏的亲信侍女,自然知晓这前来拜堂是并非武将出身的二公子而是文人之姿的大公子,然而此时此刻真见了他穿弟弟喜服的样子,也为这几分清举气度而不确定起来,莫非,莫非眼前站着的不是大公子,而是死而复生的二公子?
识茵呼吸微屏。
无它,这位新婿周身的气息实在太过肃穆强烈,令她本能地有些畏惧。
分明还没有饮合卺,她的脸却已赤红如烧呢。
彼此不言,打破僵滞气氛的是侍女带笑的提醒:“二公子,女君吩咐过了,要先却扇呢。”
谢明庭微微颔首,伸出一只修长白皙的手去,轻轻拨开了新妇面前的团扇。
笼在头顶的影子如夜幕拂落,识茵心口微微一紧,随后,团扇已被别开,一张含惊带怯的脸就此暴露在对方视线之下。
红烛热烈,仿佛那人灼热的呼吸喷薄在脸上,到底是新婚,说不紧张是假的,识茵心间慢慢地就揪了起来。
倏而,她调整好心间纷繁凌乱的心绪,抬起眸来,莞尔一笑:“郎君。”
四目相对,却都是一怔。
眼前的青年风神清令,俊朗清雅,眼凝洛水之神,眉萃春山之秀。
唯独一张冰玉似的脸,在红烛光辉下显得有些病弱的苍白,倒与流言之中的“伤重”吻合。
可即使如此,她亦能明显感觉得到,眼前的夫婿,似与去岁元宵灯会上她得见的那个不太一样。
那晚得见的他融融如旭阳。
眼前的他却清冷如夜月。
叫她忍不住要心中起疑,眼前的郎婿,真的是她的夫君吗?
况且他也似并未重伤,至少方才那迫得她头皮发麻的气势,就绝不可能出自一个伤重之人。
联想到他家中还有位双生的兄长,识茵难免心内多想。但方才他进来时,侍女们明明唤的就是“二公子”。
明烛煌煌,她眼里的紧张情绪都暴露无遗,烛火那头,谢明庭亦在打量这个母亲口中“弟弟喜欢的女子”。
她的眼睫卷曲且长,唤他夫君的时候,就如一把鸦羽浓浓密密地在空气中轻颤,似是怕他,可她眼睛里折射出的光,又分明是得见意中 人的欣喜。
一双清澈如泓的眼睛,明眸翦水,正似秋水落芙蕖。
清润秀美的长相,亦与他心中一幅未绘五官的画像契合无比,就连那一截流畅秀美的下颌,也与她相似。
却是弟弟的妻子。
至于这声音……这声音……
记忆里的清音婉婉都掩盖在元宵那夜的车水马龙之下,不能分辨。他恍惚回过了神,微微颔首。
清清淡淡的一声:“嗯。”
既见过面,接下来的一切礼仪也都顺理成章,侍女在合卺中盛上清酒,谢明庭伸手去拿,没注意新妇尚未跟上,半方合卺轻飘飘地在桌面打了个旋儿,倒将酒水泼出些许。
新婚之夜,这也算是不吉了,谢明庭目光微顿,识茵心底也是一惊,侍女忙将合卺酒重新斟上。
这回再无差错,二人各自端起被朱丝绳系在一起的半方合卺,饮尽卺中温酒。
合卺之后,这对新婚“夫妇”就算是结成了,唯剩最后一道礼仪——圆房。
识茵被侍女扶起,往湢浴去。他已先她一步起身,清清冷冷的几个字如抛金坠玉:
“我睡在外面。”
像是为了答疑一般,他又冷淡开口:“有些事,明日母亲自会告诉你。”
“只是,过了今夜你就是我谢氏的妇人了,我希望,你能一切以谢氏为重,新妇,汝可明白?”
这一声冷淡中亦有严厉,与刑狱官审犯人也没什么区别,识茵莫名有些紧张。
她小声地道:“妾谨记郎君教诲。”
他淡淡颔首,转身离开。这时身后忽然响起她的呼唤:“云谏?”
谢明庭敏锐地侧过脸。
她的声音又小下去,似是新妇含羞难以为情:“我叫识茵。‘映日成华盖,摇风散锦茵’的那个茵。家父说锦茵喻指芳草,盼我能有芳草一般美好的品质,故而取作此名。”
“我是想问……我日后,是唤你云谏还是郎君呢?”
原是为此。
谢明庭眉宇微动,下意识想说随你,略微的 停顿过后却道:“你既已过了门,便还是唤郎君吧。”
他不喜被当作弟弟,哪怕以如今的情形称呼的不同不过是自欺欺人。
语罢,动身离去。
案上摆放的红烛依旧炽热,照得屋中渐渐升温,识茵面上也慢慢攀起热意。
她听说人都对自己的名字格外敏感,故而才在静默中乍然出声试探。
但夫君的反应也没什么疑点,难道是她多想?
夜色已深,侍女们又为她打水沐浴,温暖的水流如母亲的手拂过白皙的肩胛与饱满如牡丹花萼的胸脯,沉沉热气袭上来时,识茵紧绷了半日的身子渐渐放松。
她是小门小户出身,凡事常常亲力亲为,也不习惯别人伺候。屏退侍女后,一个人靠在桶沿上想着入府以来得见的一幕幕,头脑也像是被水浸润一般,有些发涨。
这个夫君和她印象之中的不一样。
也和流言里的描述不一样。
气质秉性,怎么看怎么像传言里夫君的那位兄长。若不是方才她乍然唤他“云谏”时他应得十分迅速,她便要怀疑是李代桃僵。
可她和夫君到底只见了短短一面,此后虽通过书信,到底不曾亲近接触过,也拿不准他是何脾性。
她又想起当日元夕灯会上的一局棋。
彼时棋逢对手,她原以为棋盘对面的他是个光风霁月的男子,后来见面之时,却是个开朗赤诚的青年郎。虽说并不讨厌,但也的的确确有些惊讶。
或许,仅仅凭借一面和几封书信就先入为主,是她错了。
罢,既来之,则安之,她不会再回顾家,就必须在陈留侯府留下来。谢家是清贵人家,想来,不至于如此荒唐。
新婚次日,拜舅姑。
陈留侯府的家主陈留侯已去世十年,世子谢明庭以未婚为由不肯袭爵,因此说是拜舅姑,实际上能拜的也就只有婆母武威郡主一个。
她出身凉州叱云氏,是凉州公的堂妹,生父在三十年前朝廷平定秦州叛乱时战死,其母也是女将,一同战死,彼时的天子可怜这孤女无依无靠,特封武威郡主,御赐九节鞭,表彰其父母的忠义。
叱云氏这一支也是魏朝的老牌勋贵了,自太|祖打天下时便跟随左右,忠心耿耿,世代镇守凉州。也是因此,先前那位凉州公叛乱之时,太上皇并未追究到整个叱云家族的头上,又因其女大义灭亲,及时阻止兵变,仍命她袭爵凉州公,只是免了世袭。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又在为女帝挑选丈夫时,选了凉州公与中书丞的独子周玄英。
换句话说,国朝的“皇后”是武威郡主的堂外甥,叱云氏,是真正的皇亲国戚。
她将门出身,青年守寡,脾气也不好,独自一人将两个儿子拉扯大,传言看儿媳的眼光是很挑的。
后来,她选择了小家碧玉出身的识茵,引得京中一片哗然。加之识茵父母双亡未过门而夫婿伤重,一时之间,京中又有骂她“丧门星”的闲言传出。
这些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识茵早在闺中便已背过,熟稔于心,既已嫁过来,她也无一般新妇拜舅姑的忐忑,晨起梳妆后,略用了些膳食,欲往主房去。
与卧房只相隔一道碧纱橱的书房里,昨夜新婚的夫婿已在等她了。
他倚在窗下的软榻上,脊背挺直,如松如鹤,一条腿微微曲起,手搭在膝盖上,左手则擒了本行军打仗的兵书正专心致志地看着。
——自小被誉为“神童”的状元郎在扮演弟弟一道上自也天赋异禀,除却原本冷厉的性子,近乎无所破绽。
褪去了昨夜的玄红喜服,更为贴身的箭袖开胯袍勾勒出青年郎君精瘦雄健又无一丝赘肉的躯体,四肢修长,身姿伟岸,赏心悦目。筋肉内敛的走势中似蕴着无尽力量,的确像个武将,不像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
识茵只抬眸看了一眼便低下眉去,昨夜那诡异的猜想由此由消弭一些。
谢明庭将新妇子的猜疑看在眼中,只淡淡一拧眉:“走吧。”
二人并肩往临光院中去。
武威郡主心情不错,面上笑盈盈的,接了新妇的茶后,又将早已备好的石榴纹红玉手镯与她戴上:
“你既和麟儿成了婚,便算是我们陈留侯府的人了。我没有女儿,你既嫁过来,我便将你当作女儿一样疼爱,盼你日后,能与夫婿恩爱白首,孕育子嗣,早日为侯府开枝散叶。”
婆母和蔼可亲,一点儿也不是传闻里的暴躁骄纵,然提起生子之事,识茵少不得做出些羞赧之态,羞答答地朝身侧芝兰玉树一般的夫婿看去。
昨夜,他们并未圆房。对于这位“夫婿”,她还有一肚子的疑惑。
既是内宅之事,必然瞒不得婆母的,不知婆母此时提来是在敲打什么。
谢明庭自知母亲打的主意,然当着新妇含情脉脉的眼神,也无法出言辩驳,只面无表情,似乎不曾闻见。
武威郡主在心里恼他忤逆,面上笑容慈爱:“好了,新妇害羞呢,麟儿你先下去。”
——陈留侯府双生子,一名明庭,小名鹤奴,字有思;一名云谏,小名幼麟,字仲凌,郡主常以“麟儿”称之。
谢明庭起身,转身即走。
识茵将他的冷淡看在眼里,有些尴尬,又有些失落。
诚然她来时是做好了吃苦的准备的,但她怎么也没想到,夫婿不是传言里那般伤重,却似完全换了个人。
她原想着,若他真的伤重她也会安安分分陪他走完最后一程,守孝完成后再离开。
现在看上去她倒似不用守孝了,不过以他对自己的冷淡,兴许将来会和离?
“你是不是好奇,你夫婿为何变得这样沉默寡言?”
武威郡主的声音在身前响起,识茵回过眸,眼中恰到好处地蕴出了几分伤怀。
“其实你们之前也见过,云谏他……从前不是这样的。”武威郡主叹着气说,“是,如你所见,他没有如传言中那般重伤,那是因为他在江南替圣上办事时,他最亲近的朋友替他挡了一劫,然后,他的性子便成这样了。”
识茵一惊,想起当日灯火重重中眉眼含笑、意气风发的青年郎,再一想到如今这个冷漠孤僻、几乎不与外人交流的青年,心脏处也如被人抓了一把似的,生出丝丝怅惘。
原来,夫君他竟是、竟是遭遇了友人的死才性情大变的么?
见瞒过她,武威郡主又趁热打铁地道:“你放心,他只是难以走出友人的死而已,绝不是不喜欢你。”
“夫妻间过日子还要多磨合,既然他性子冷淡,你就得多主动些、多体贴他些,争取早日把房圆了,生个大胖儿子给母亲抱。阿茵,明白否?”
她说得太直白不过,识茵面上也不由得晕出红霞。
她没那么矫情,既为人妇,夫妻之事是少不了的,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新妇知晓了。”她低声地应。
不过话虽如此,一个多时辰后,她回到房中,面对着婆母差人送来的一挪有关夫妻房事的书籍,还是有些脸热。